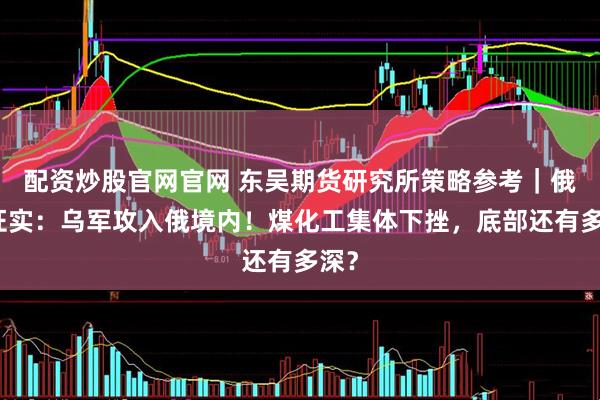那是一个临近中秋的夜晚,风吹过铁像寺水街,诗人何小竹读了一首关于月亮的诗。紧接着是桑格格,她的诗歌里有未洗的盘子、160岁的牡丹和兔子耳朵。吉木狼格的三个老朋友喝了三杯酒,想起了过去的时光和少女。
单于写下《秋天三章》,余幼幼在一滴水珠中看见了人民中路二段,然后,那些叫《空空儿》的诗选念响,白姥姥说,她有了新的名字,叫白姜。
阿库乌雾来了,身着盛装,用彝语呼唤,撕裂地、悠扬地、铿锵地。海桑轻轻地坐在长凳上,呢喃道“打我记事开始,爷爷就是个老头”。宁不远回到了6月11日,那个在雨中奔跑的下午……
城市日常总有涌动,就像过去几天,我们在诗与歌的交互中捕捉到的这份闪光。它来自YOU成都的好朋友远家与铁像寺水街共同呈现的“诗与歌”2025“家门口的远方”。
这个夏天,水街刚过完12周岁生日,作为公园式非标商业街区的代表,它以川西文化为底蕴,融合艺术、商业与自然,自诞生之初便在地域文化的传承中,探索、发现多元生活方式与高品质消费场景的可能性。
展开剩余94%同样,说起“诗与歌”,你或许也并不陌生,这是远家连续举办5年的市集品牌,像秋天的序言,总给人期盼。过去的日子,我们曾追着一朵云,抵达明月村,在歪脖子树下赶集、聊天、逛展、听音乐、吃香喷喷的大锅饭。
而这一次,水街携手远家开启2天1夜的精神漫游,汇聚来自全国各地的50余家生活美学品牌,20余位/组音乐创作者、美学实践者与诗性灵魂共赴其中。
它像极了一场城市即兴,由“诗与歌”筑起,从“远方的家”到“家门口的远方”,那些花木、鸟鸣、云朵、炊烟和居住在精神的蠢蠢欲动,在乡村与城市间迁徙、漫步,塑造着一种难以被忘怀的日常。
01
乘着阳光、云朵与雨雾,
从明月村到铁像寺水街。
“白小莎”,当李建国的声音在明月远家的屋顶天台响起,回荡在耳畔的,不仅是相距十年的重逢,更是跨域一生的羁绊。
这席由演员陈浩与宁不远担任主角的话剧围读,围绕《情书》展开。我们曾在市区的一家小剧场看过这场戏,而当演绎的场域转换到乡村,以围读的方式呈现,竟生出了些质朴的新意。
夜空下的屋顶,分外静谧,演员吐出台词,和挂在天边的星星一同闪烁。观众们拾阶而坐,这是他们今年相逢在“诗与歌”的第二个夜晚。
天空刚刚下过一场雨,那时,他们打着透明伞跟着果子和娜娜在雨中跳舞,脑海里或许闪过一丝胆怯,但很快便散去,踩着快乐的舞步,剩下的,只有“岛屿”交融的热情与自由。
白天的市集和摊主开放麦也很热闹,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在绵延的草地上支起风格各异的小摊。这个下午显得格外珍贵,因为明天,他们就将一同迁徙,抵达“诗与歌”的另一个目的地——铁像寺水街。
从标志性的牌坊下走过,植物染的着色之下,有流动的“天空”,也有“毛姆的月亮”,而它隔壁的那张旧书桌,则让人想起了伍尔夫《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》。
再往前,小摊像满载生活灵感的部落一路蔓延,他们不仅贩卖商品,更交换情绪与各自主张的生活方式,成为“诗与歌”漫游中最为鲜活的呼吸。
喏,铁像寺水街的不远,打包了浓郁、明媚的色彩,邀请匆匆过客带一束秋天回家;有布营造将在自然中采集到的材料组合,编织成独特的包袋、装饰、会唱歌的音乐摇铃和女巫的魔法瓶。
二模丸从古蜀文化中提取元素,制作成可爱的模型;俏山将生活中的灵感变成了毛毛虫、梨小孩和放在哪里都超合适的手工纽扣。
从桂林远道而来的芽小七将传统文化用于创新穿戴,他们在当地找了300多位绣娘,对那些承载着悠久文化的虎头、舞龙、醒狮进行重新设计。
与主题最为契合的大概还有李迪,他在旅行途中突发奇想来摆摊,没有个人品牌就以自己的名字命名,宜兴的朋友寄来了紫砂壶,景德镇的朋友寄来了茶具,杭州的朋友寄来了咖啡和公道杯,云南的朋友寄来了茶叶,靠着远程众筹将“远方”变成了“家”……
当然,除了市集,这场漫游,还给我们带来了数场沉浸式体验以及数不清的现场即兴:
田鼠大婶分享了在泥土里生长的庄稼和诗歌,诗人文杰、单于、媃迦、疆、樊弘、向烨辉以“野有明月”为题,开启诗歌之夜,Shun与Yuuki在草地上与我们再次见面。
何玉林与马海龙奏响了秋天里的歌谣,低苦艾刘堃在清晨日暮里大声歌唱,绿叶红花乐团唱响了故土、远方与花朵,莺桥和狗咪在旋律中走进小径分岔的花园。
诗人海桑讲起了那颗埋头写诗的石头,毛继军、朱星海、牛园、宁不远、余明旻从品牌出发,铁娃公社和驻色对话“活出来的非遗”,茶画家与入云屋聊起了生活茶事……
02
我们的生活,
为什么需要诗与歌?
让人意外的是,本以为在追求速度与效率的时代里,诗与歌似乎始终是小众,但在这场活动中,我却遇见了比想象中更多的人和可爱、同频的灵魂。
拙匠和小薇是一对夫妻,他们住在成都天府新区天平镇,一个做陶,一个染布,经营着一家叫做“拙闲居”的品牌,他们一年只出一次门,而这唯一,便献给了“诗与歌”。
有客人记得,去年来,小薇还大着肚子,再次见面,摊位上多了个孩子。
她整天呆在院子里,看到一朵花开出来,偶遇一朵鸡纵菌,窗户上什么时候悄悄挂上了丝瓜,这里一条,那里一条……不知怎的,诗自然而然就流动了出来。
同样把日常过成诗的,还有来自杭州的桃桃。2014年,她从父亲手中接过一杯龙井茶开始了“茶画家”的故事。
在那座电商事业蓬勃的城市,她先后扎进两个园区,后来,下定决心回到乡村,从自然和节气里汲取灵感,秋天摘桂花、做柚子酱,冬天躲在炉子旁烤火……
在她摊位上,我买到了最后一份“绝绝紫”,上面印着陀思妥耶夫斯基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中的那句“要爱具体的人,不要爱抽象的人。要爱生活,不要爱生活的意义”。
桃桃喜欢在做设计时融入喜欢的诗歌或文字,她自己也写诗。她说生活不能没有诗,那是中国人骨子里的东西,自己很容易被它们散发的能量打动。
像她们这样的摊主还不少,他们大多在带货外,怀揣一份对精神世界的热爱,这些物质之外的东西也包裹着他们的摊位,吸引了很多同频的顾客。
他们之间流通的东西,也压根不是商品本身,而是背后某种对于生活的共识。
所以,我们为什么需要诗与歌?我试图将这个问题抛给在场的人。
诗人何小竹分析道,80年代的人喜欢诗歌,是特殊年代之后形成的现象,到了今天,诗歌或者说更大一点的文学看似被边缘化了,但其实是回到了它们原本该有的位置。“它就是这样被一部分人喜欢,被一部分人写它、读它、听它。”
不过,在成都当诗人是一种幸运。他笑道,这是为数不多可以在饭桌上大胆承认自己是诗人的城市,清代学者李调元就说过,“自古诗人例到蜀”,它源于这座城市与诗歌文化之间的双向奔赴。
作家桑格格在活动中带来了新书《打泉水去》,她认为,诗与歌是人类的正常需要,甚至是生理需要,“它是我们所需要的精神的,抽象的,能够穿越眼前日常的一种慰藉”。
远家创始人、写作者宁不远曾写过一本叫《把时间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》的书,在她看来:“诗与歌看似无用,对人的滋养却不可限量。”
建筑师余明旻把诗与歌看作理想主义最理性的坚持,它指向日复一日的真诚和认真的态度,并不能靠简单的理想和情怀构筑。
音乐人贰爷和他的好朋友KUN在诗与歌交互式演出中带来了一段融合古典韵味与现代风格的即兴,期待在音乐中表达一种“时间的流逝”。
“节奏越来越快的时代,诗与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不可替代的‘慢’与‘深’。”他说:“让我们能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,也希望自己能拥有这份精神上的优雅与力量。”
03
在日常中共赴,
远方的家和家门口的远方。
的确,穿梭在现场,时间是一股潜隐的力量。
相聚在现场的,大多是些靠着双手,一点一点打磨技艺的手艺人,在别人眼里不值一提的小事,他们默默做了十几年,甚至更久。
就像“诗与歌”背后的远家与铁像寺水街。
今年,是远家做衣服的第15年,也是水街开街的第12年,他们共同将“诗与歌”搬到了城市,第一次在一条街区里呈现。
它不仅是一处非标商业,更是一座彰显在地气质的文化商业。近年来,为深挖蜀地文化基因,水街聚焦首店经济与业态升级,探索多元生活方式,首店品牌占比已超60%。
其中,远家倡导朴素、节制的生活方式,主张“在物质世界里寻找精神的含义”。2024年的某一天,它从乡村来到城市,在水街开设了自己的城市首店。
如果说,明月远家是“远方的家”,那水街远家便是“家门口的远方”。此次“诗与歌”的主题,正好呼应了这个属于“家”的概念。
其实,铁像寺水街,又何尝不是一座更大的“家门口的远方”。
身在国际城南的它,以独特的“古建+外摆+临河”创新空间布局,在寺庙、茶铺、咖啡、展览等多元生活方式中回归“附近”。
从远家出发,沿着流水一路寻访,在距离街区中轴线稍远一点的地方,有一座屋子。这是李白鹿的入云屋,一个由味道出发的生活学品牌。
它的名字来自杜甫的“锦城丝管日纷纷,半入江风半入云”,李白鹿将最后一个字落入“屋”中,因为屋子小小的,给人一种回到家的感觉。
作为邻居,他也加入了“诗与歌”,在一场对谈中,他分享了自己关于真的感受:“真善美中,真最为重要,投入到真实的生活中去,生活自然会给你反馈,哪怕平凡,依然具有生命力。”
我想,这也是我们在家门口期待远方的原因,因为那里有远意,也有普通的我们和真实的生活,而当我们站在水街,站在远家,那里,变成了这里。
正像在活动最后,钢琴与小提琴奏响合鸣,一群素人“模特”穿着远家的衣服,在聚光灯照耀下,开启了一场走秀,从“家门口”走出来了:
在成都生活20年的台湾美食家孙阿姨,会做包子也会唱歌的牟子,退役的射箭冠军豆豆,在村里开书店的蘑菇,在蒲江做甜品的雅丽,自由职业者波莫石牛,公司职员大苹果,心理疗愈师大曾,摄影师米米,远家联合创始人CEO贝壳一家,还有前员工小朱和他的心上人……
●
在水街,遇见向往的成都生活
● ● ●配资炒股官网官网
发布于:四川省鑫东财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